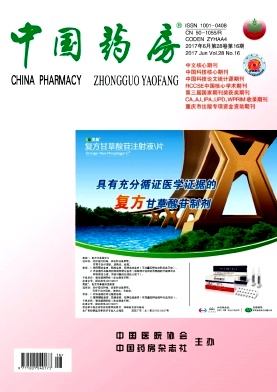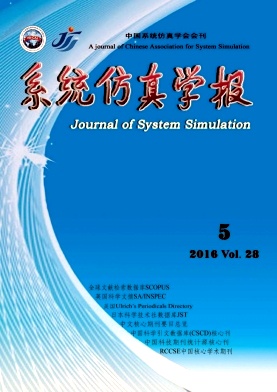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论文【一】
《增补搜神记》糅合了各种民间神灵,虽图文并茂,然刊刻因陋就简,带有通俗读物的特性。李丰楙认为《新编连目搜神广记》(下文简称《搜神广记》)是“民间通行的搜神类书”[1],源于其杂抄各类资料并带有“儒释道”的区分,基于《搜神广记》而成的《增补搜神记》[2]自然有相同特点。《增补搜神记》中的故事都以“神”为主线,可归为道教仙传的一种。李丰楙还认为:“道教中人撰述仙真传记,常有一个共通的情形:就是选用多种材料,却多不註明其来源,因此探索任何一种杂传体传记,首先要辩证资料的袭用关係。”[3]《增补搜神记》中收录的神仙事蹟一直在民间流传,且源流难考,诚如叶德辉所说:“或史传不知其人,或有其人而无其事,大都供文人之藻翰、挥尘之谈锋,前人附会而言之,后人因缘而述之。”[4]故分析其中仙传故事的来源尤为重要,下文将试以“王侍宸”为例,说明其中的故事情节大约出自哪种文献的记载,是怎样由传世文献匯集、加工、改编而成。
1、王侍宸
王侍宸就是《歷世真仙体道通鉴》、《列仙全传》中的“王文卿”,宋徽宗时的道士,与林灵素齐名。王文卿为宋时人,文中又指明“元时始建祠”,故宋之前的文献资料无其记载,其事蹟首见于《夷坚志》:
宣和中……葆真宫王文卿法师善符箓。……王师,建昌人 。[5]
建昌王文卿既以道术着名,其徒郑道士得其五雷法,往来筠、抚诸州,为人请雨治
祟,召唿雷霆,若响若答。[6]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间,不但以道术显,其相人亦妙入神。[7]
傅选为江西副总管时,邀临川王侍晨来豫章,从学雷法。王甚恶其人,然念凶德可畏,不敢不与,但教以大略……(选)愤王传术不尽,欲募刺客加害。王已先知之,怒曰:“彼为我弟子,而谋射羿,岂宜使滋蔓得志哉!” 于是以法飞檄,悉追其所部灵官将吏。选所行法从此不復神。[8]
王文卿侍晨,已再书于前志。绍兴初入闽,不为人所敬。……因府治设醮祷雨,命为高切,……己独仗剑禹步于下。方宣词之次,星斗满天,已而暴风驾云,亦从西北隅至。烛尽灭,震霆一声,甘雨倾注。 (福州刘存礼说。) [9]
《夷坚志》中的王文卿普收徒衆,善符箓法术,能唿雷唤雨,驱使鬼神,时人视为神仙。《夷坚支志》已提及其设醮祷雨之事,但具体情节与《增补搜神记》不同。在《夷坚志》中,借黄河水求雨的是林灵素:
京师尝苦热,弥月不雨,诏使施法焉。对曰:“天意未欲雨,四海百川水源皆已封锢,非有上帝命,不许取。独黄河弗禁而不可用也。”……林取水一盆,仗剑禹步,颂呪数通,……有云如扇大起空中,顷之如盖,震声从地起。……雨大至,迅雷奔霆,踰两时乃至。[10]
王文卿成为借黄河水求雨的主角,则首见于《宣和遗事》:
宣和二年……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诏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应。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龙君,皆奉上帝敕命,且停行雨;独黄河神未奉睿旨。”……翌日,升坛祝曰:“大宋皇帝借黄河叁尺水,以济焦枯。”不移时,甘雨大作,遍地皆雨黄雨,以应黄河之水。[11]
《宾煺录》中求雨的主角也是王文卿,同时交代出他和林灵素的关係:
京师大旱,命灵素祈雨,未应。……灵素请急召建昌军南丰道士王文卿,……文卿既至,执简敕水,果得雨叁日。上喜,赐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12]
如此,借水施法的主角就由林灵素自然地转换成王文卿。且通过两者对比,更凸显出王文卿法术高于林灵素。这跟南宋初林灵素在政治上的失势不无关係。
《歷世真仙体道通鉴》也提及了此事,虽情节大致相似,但是对王文卿设醮求雨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王侍宸”中“仗剑噀水”一词就由此而来:
先生奏乞剑水盂。奉劫赐水盂并剑,先生嘤水一口,祝云:“大宋皇帝命臣祈雨,雨要雾霜,风要拔树,扬州千里之内,并要霑足。借黄河叁尺。急急如律令。”[13]
本则故事的直接来源应为《大明一统志》卷五叁建昌府“王侍宸祠”,记载如下:
王侍宸祠,在府城内玄妙观。侍宸名文卿,尝遇异人授以道法,能召风雷。宋徽宗朝号为金门羽客凝神殿侍宸,赐赉一无所受。时扬州大旱,诏求雨,乃仗劔噀水曰:“借黄河水叁尺。”后数日扬州奏得雨水皆黄浊。元时始建祠,至今灵应益着。[14]
《增补搜神记》除了“生有相骨,有道者器之。长而游四方,履歷几遍宇宙”、“执牲帛而乞灵者络绎于道”等细节有所增补,其他方面的描述与《大明一统志》基本相同。且《宣和遗事》、《歷世真仙体道通鉴》都是先提王文卿求雨一事,后才写其因此受封,而《大明一统志》与《增补搜神记》均先写其受册封,后谈其求雨,足以可见后者乃直接摘录前者并增删拼接而成。《叁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王侍宸”在文字上与《增补搜神记》完全相同,但所配图像各异,《增补搜神记》中的配图描绘的是王文卿遇异人得授道法之事,《叁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配图则描绘的是王文卿借黄河水求雨之事。
2、结语
仅“王侍宸”一则故事的文献来源,就包涵了志怪小说集(《夷坚志》)、笔记小说(《宣和遗事》)、神仙传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等,可推见《增补搜神记》中故事来源之杂。且其中收录了许多宋元以后新产生的神,多是由真实人物演化而来。这些神大多流传民间,古籍文献对其记载较少且难成系统,故本文试图大略梳理“王侍宸”故事产生的来龙去脉,希望借此对民间信仰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注释:
[1]《提要与总目》,《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一辑)》第—册,臺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1页。
[2]关于《增补搜神记》与《搜神广记》之间的关係,已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如贾二强《叶覆明刻〈叁教源流搜神大全〉探源》一文认为《增补搜神记》“按其体式、诸神次第及文字异同,当源出元本《搜神广记》。”(《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二集)》第232页,陕西师範大学出版社,1992年)孔丽娜《元刻〈新编连相搜神广记〉诸神故事来源考》一文将《增补搜神记》与《搜神广记》进行比勘,发现《搜神广记》中的57个神全为《增补搜神记》收录,且其事蹟是在细节上有所增删,部分增加楹联、赞诗等,变动很小。所谓《增补搜神记》中的“增补”,无疑就基于《广记》而来。(陕西师範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侯婧《明万历仙传类文献研究》一文认为《增补搜神记》在《搜神广记》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并摘录出其独有的条目。(南京大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3]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臺北:臺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0页。
[4]见叶德辉“重刊绘图叁教源流搜神大全后序”,《绘图叁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354页。
[5](宋)洪迈撰《夷坚志》, 夷坚甲志卷八“京师异妇人”,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册第65-66页。下引版本同。
[6]夷坚丙志卷十四“郑道士”,《夷坚志》第二册第487页。
[7]夷坚丁志卷六“王文卿相”,《夷坚志》第二册第582页
[8]夷坚支志乙卷五“傅选学法”,《夷坚志》第二册第832-833页。
[9]夷坚支志丁卷十“王侍晨”,《夷坚志》第叁册1049页。
[10]《夷坚志》丙志卷一八“林灵素”,《夷坚志》第二册第518页。
[11]佚名:《新刊大宋宣和遗事》元集,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16页。
12](宋)赵与时:《宾煺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13]《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叁《王文卿》,《道藏》本第五册第412页-414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影印本。
[14](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叁秦出版社1990年,第835页。
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论文【二】
一、人生而痛苦
无论是苏童,亦或者鲁迅,他们的人生似乎都充满了太多的黑暗。鲁迅的一生是坎坷的,少时家道中落,父亲病重,遭人冷眼。成人之后,先是不满于包办的爱情,而后兄弟失合。再后来困于疾病长达数年,期间更是被无数不理解的人所指责。而苏童亦是如此,自小家庭贫困,九岁时患上了严重的肾炎和并发性败血症,差点死掉。对于儿童来说,这种经历的影响是一辈子的。苏童自己就曾说,“我相信托尔斯泰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终都要回到他的童年。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回顾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发现自己对世界感触最强烈,最文化的时期就是青少年时期。”[1]因此对于他作品中出现的那些阴暗死亡的气息,或许是他的一种写作惯性。可是无论鲁迅还是苏童,他们都意识到了个体生存的这种痛苦性。
在《孤独者》中,祖母辛苦一生,把魏连殳抚养长大,到临死之前还惦念着魏连殳,她最后留下的话是“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连殳的呢?……”[2]一个女人,终其一生抚养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抛弃中间的心酸与孤独,到最后也没有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孩子,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而魏连殳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一个真正孤独的人,他的孤独只能通过长嚎来发泄,像一匹旷野里受伤的狼,在惨伤中夹杂了愤怒和悲哀。透过这篇小说来反观苏童的《河岸》,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慧仙,库东亮,库文轩都是类似于魏连殳那样的弃儿代表。他们的家庭从开始就不完整,男主人公库文轩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种身份认同。库文轩开始被大众认可为革命后人,是因为屁股上的鱼形胎记,这种认可本身就是荒诞的。库文轩的儿子库东亮,是整部小说中最悲哀的一个人物,他有父母,可是却没有得到家庭之爱,反而是变态的管制和压抑。他爱慧仙,可是心理上的障碍让他永远都不可能亲口对慧仙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他原来是岸上的人,最后却被告知失去了上岸的自由,永远的漂流在船上。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慧仙亦是人生而痛苦的代表人物。她在寻母失败后,寻找权势依附,结果被抛弃,而后妥协于现实嫁给他人。
二、他人即地狱
叔本华说,“这个世界只是‘地狱’----在这里,人类既是被折磨者,同时又是折磨别人的魔鬼。”[3]每一个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或多或少的与他人发生联系。每个个体自身对欢乐与苦痛的感受有时候又是直接地来源于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又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来进行深层次的理解。第一种关系是有些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第二种是有些人对待他人没有怜悯与同情之心,对于他人所经受的苦难,以一种“看客”的身份来加剧别人的痛苦。第三种是人与人之间的无形牵连,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对这种关系最形象的表述。第四种是更为复杂的一种关系,有些人想要通过践踏别人的尊严来获得自己的快乐,可是到头来却发现这样的做法,反而加剧了自己的痛苦。最后的一种关系是,有些人对于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会把期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并且通过变态般的管教,来达成自己的欲望。最后两种关系都是典型的他人即地狱,彼此折磨的代表。
这五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都可以与鲁迅和苏童作品中的人物一一对应起来。像是《药》中的华老栓一家人为了救自己的儿子,而对革命者夏瑜的生命丝毫不关心,就可以很好地说明第一种关系。对于第二种关系,在他们两人的作品中都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人。《药》中,夏瑜本来是一位有志青年,想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甚至在牢狱中还不忘记劝牢头造反,可是他的行为在民众眼里却是可笑的,甚至被别人当做疯子。最后更是被残忍地对待,在被惨遭杀害后,也变成了这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河岸》中这样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了,河与岸本身就是一组对立的词。在小说中,岸上的人看不起河上的人,认为他们肮脏,下贱。然而河上的人却有着美好的品质,他们勤劳而又有包容心,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人。反而岸上的人要更邪恶一点,他们冷漠,奸诈,欺软怕硬,甚至当别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会以落井下石的方式对其进行攻击,而不是通过劝慰给他人带去温暖。
对于第三种相处模式,在《河岸》中,随着库文轩权势的跌落,无论是乔丽敏,库东亮,还是与库文轩有过纠葛的那些女人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第四种模式,在魏连殳和乔丽敏的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魏连殳为了“多活几日”,被迫地去依附权贵,又因放不下自己内心的“坚守”,只能痛苦的活着。在活着的同时,改变了以往对待孩子的态度,“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总是低声下气的。近来可也两样了,能说能闹,我们的大良们也很喜欢和他玩,一有空,就到他的屋里去。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们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4]通过魏连殳态度的转变,现在的这种与人相处的模式,就是第四种模式的真实写照。最后的那种模式,是《河岸》中库文轩与库东亮关系的典型表现。库文轩因为自己生活作风问题而被“流放”,因此在他看来性是一种邪恶的东西,绝不可以触碰。因此他疯了一般的监管者库东亮,不允许他有正常的生理反应,甚至不允许他把手放到被窝里睡觉。在这样变态的压制之下,库东亮只想逃离这样的关系,因此在小说中提到了库东亮的多次奔跑。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跟着通往“幸福”的便车离开,“五毛钱去幸福。到幸福去。那么好的地方,那么便宜,可惜我去不了”。[5]
三、永恒的幸福是虚无
对于幸福的追寻是每一个个体都会去做的事情。可是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仍然只是停留在追寻的层面上,他们焦虑、彷徨、失望、痛苦,甚至有些人追寻到抑郁。其实幸福只是一瞬间的感受,当你用心体会的时候,你便得到了幸福。而大部分人所追求的那种永恒的幸福,都是指向了虚无。“《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从开始对孩子看法的转变,到后来迫于生计,违心的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才发现自己所寻找的那种理想社会的荒诞性。然而即使他做出了妥协,他的内心仍然是抗拒的。或许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如此荒诞的世界,因此他只能通过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方式来面对它。像他自己内心的独白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我真的已经失败,──然而我胜利了。[6]同样的在小说《河岸》里,也体现出了这种追寻的虚无性。而苏童自己也说,《河岸》是一部寻找的小说,他们首先是寻找母亲,这是一个共同点,其次是寻找身份,寻找家和乡土,寻找爱,或者干脆说他们必须寻找天堂。其实所谓的寻找天堂就是虚无意义上的永恒幸福。库文轩对母亲的寻找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势寻找。至于库东亮,则是最另类的幸福追寻者,是一种可怜的存在,他甚至连幻想幸福的权利都没有。他深爱慧仙,每当他对慧仙抱有幻想的时候,对自己连说三声“空屁”,那种强烈的生理反应便会荡然无存,这是一种极端的自我戕害,自己都没办法救赎自己,自己设定了自己悲哀的人生,自己放弃了自己。
结语:
鲁迅和苏童,这两位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因热衷于探索人的灵魂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共鸣。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了对人生存处境的思考,而且在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某些方面,苏童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在继承的同时,又开掘出了一些新的东西。长篇小说本来就包含的多一些,这也无可厚非。他们的作品结局通常都很惨烈,但是通过思考,我们又可以理解到作家通过作品,所传达给我们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可以让读者们面对如此险恶的世界,仍然有生存下去的勇气,仍然爱这个残缺的世界。